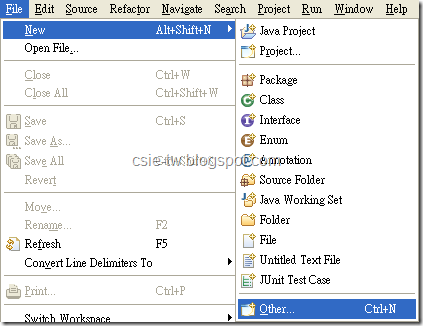Mark Blaug (1994): “Not only an economist: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of a historian of economic thought”, The American Economist, 38(2):12-27.
高景仲譯 賴建誠校
我決定唸經濟學,是受到Henry George與Karl Marx著作的影響。1944年我17歲,唸紐約市的Peter Stuyvesant中學,修了一門商業的課。學期的最後一週,老師帶我和幾位比較優秀的學生,到鄰近的Henry George School參與一場講座。主題是在解釋,如果地租沒有限制地成長,就會造成貧窮、戰爭,以及其他現代文明的弊病。Henry George在很久以前,就診斷出這個病灶,並提出解決良方:單一地租的「沒收性」徵稅!講座結束時,我們都得到Henry George的免費著作《進步與貧窮》(Progress and Poverty,1879)。這本書我讀得一頭霧水。幾年後,當我讀到Ricardo的差額地租理論時,發現George的理論來源,因而感到一陣興奮。
1馬克思主義的影響
《進步與貧窮》引發我的興趣,但並未讓我信服。不久後在紐約大學讀大一時,我結交幾個左翼同學,他們先介紹我看 Lenin與Stalin的小冊子,之後是Marx與Engels的大部頭。我深深被這些文章折服,幾個月內成為馬克思主義者,Marx的虔誠追隨者。
我現在試圖回想,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到底是怎麼回事,可以那麼快就改變我。我想那是一些特質的組合,這些特質可以充分說明我這個人,以及馬克思主義。首先,主要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文章中,閃耀著那種絕對擁有真理的氛圍。特別是集大成的Lenin與Stalin,以執拗辛辣的語調,對付敵營的知識份子。第二,馬克思理論百科全書式的觸角,感覺這是個社會的普世科學,的確是一種哲學史以及自然的哲學。無論是最近的選舉結果,或是法國大革命的成因,或是古希臘王朝的傾覆,或是Rembrandt為何對光影對比(chiaroscuro)情有獨鍾,或是Beethoven最後的鋼琴協奏曲第102號為何只有兩個樂章,或是Gothe在《浮世德》(Faust)最後要表達的是什麼,都有可能在馬克思主義中解釋。年輕的我頗好發高論,馬克思主義就像為我量身定做:它可以讓我大言不慚地,對所有題材發表自以為是的議論。
馬克思主義教我經濟決定論。根據經濟決定論,經濟利益與經濟力量,是所有社會與政治衝突的基礎。進一步推論,所有事物最終都可簡化為經濟學,經濟學因而可以稱為社會科學之母。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六個月內,我決定必須讀通經濟學。大二那年我修了第一門經濟學,我清楚地記得這是很重的學科。我很高興還能記取自己唸經濟學的困難,因為這使我成為更好的老師。
這些還不足以完全說明,馬克思主義對我的吸引力。對我來說,馬克思主義引人入勝之處,在於它的概念工具、專有名詞與各類的精緻術語;以及無數的(古猶太法統)區分,如「底層」與「上層結構」、「生產模式」與「生產關係」、社會行為的「策略」與「方法」、社會經濟體系的「矛盾衝突」與「對立整合」等等。一旦掌握技術性語言,服膺馬克思主義,就可以創造一個論述的次文化。在這個次文化中,不誇張地說,只有馬克思主義者能了解你。簡言之,馬克思主義讓我初窺,知識社群自我哺育的學術文化。
我並不只是個純知性的馬克思主義者。加入美國共產黨、出席政治會議、參與政黨示威,這些我都做得意興闌珊,因為我不太熱衷參與組織活動,然而卻也短暫地經歷一段真實的政治活動。過程簡短,是因為我天生反骨,很快就被逐出共產黨。1945年當大戰接近尾聲,同盟國佔領德國的問題浮上檯面,成為政治議題。為了讓美軍永久駐在德國,美國總統Roosevelt提出戰後軍事召集建議案,得到美國共產黨主席Earl Browder的背書。Browder因而被若干黨員視為異端。Stalin出面反對羅斯福的政策,Browder的命運也就此底定:主席的職位被拔除並逐出共黨,瞬間成為「不受歡迎人物」。幾個共黨大學生,替Browder收集陳情書,經過一番考慮我簽署了。之後我被傳出席共黨審判庭,由於應訊時未表悔意,旋即被開除黨籍。從那時起,許多黨內友人與舊識,不只不跟我講話,甚至在街上相遇也裝作不認識。從未加入陰謀(或準陰謀)組織的人,很難相信黨內同志相煎的速度既快又急。1945年時,美國共產黨在政治上無足輕重,我的經驗顯得荒謬,但對當時的我來說,這是對左翼政治現實的痛苦覺醒。
雖然在1945年時,我已非搖旗吶喊的共產黨員,之後卻要用了至少七、八年的時間,來擺脫馬克思主義餘緒的桎梏。1945-52年間,我頭也不回地與共產主義漸行漸遠。我清楚記得,The God That Failed: Six Studies in Communism (1950)這本書對我的影響。Arthur Koestler、Ignazio Silone、Andre Gide、Richard Wright、Louise Fischer、Stephen Spender這六位作者,都是出走共產主義的「旅伴」。事隔多年,我還記得與知名共黨叛黨份子,一起幻滅的那種糟糕感覺。捐棄先前的信仰,而沒有踏上「完全不信」這一步,是很玄妙的。對我來說,這一步的動力來自1952年夏天,胎死腹中的東德「革命」:東柏林人幾乎推翻蘇聯扶植的東德政府。1952年5月我去柏林旅遊,見證了反東德政權的強烈憎恨。回到倫敦後,我從共黨的平面媒體,看到革命爆發與蘇聯坦克鎮壓的報導。我一直知道,共黨報章能睜眼說瞎話,但我之前閉著眼睛,讓謊言持續上演。像我這種「真正信仰者」所經歷的幻滅,就像泡過熱水澡後的當頭冷水淋浴。
當年身為共產主義者,所相信的、剴切力陳的、全然信服的事,現在想來讓我羞紅耳根。例如我記得如何為「莫斯科大審」的史達林版辯護。這個版本指出,住在巴黎和墨西哥城的Trotsky,籌劃在蘇聯境內進行大規模破壞,甚至要危及蘇聯軍事高層。儘管讀了Arthur Koestler的Darkness at Noon,我把它斥為資產階級的文宣。這讓我從此以後,對強烈主張的信仰存疑,也讓我比原來的自己更能容忍。現在每當我聲稱某件事絕對真實,總會悄悄對自己說:「是的,就像莫斯科大審。」
我棄共產主義如敝屣,但揚棄馬克思主義則還要更多時間。從某個意義而言,壓榨、異化、不平等這些大主題,依然揮之不去。當然,經濟學唸得越多,我就越不相信馬克思經濟學。我很快就看出,馬克思對社會主義經濟難題的掌握,程度是可笑的。他真的認為,社會就像大街角的雜貨店,出現的事情頂多是會計問題 。此外,馬克思的經濟預測,絕大部份都錯得離譜。在他死前,對無產階級未能推翻資本主義,顯然深感失望。但我還是花了很多年,看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核心深層謬誤。即使在今天,馬克思主義者,甚或前馬克思主義者,還是看不出這個謬誤。這是個非常有趣的謬誤,很聰明地被隱藏在《資本論》裏,千分之一不到的讀者曾注意到。這個想法是:經濟體中每個產業,都有相同的剩餘價值率。簡言之,資本家每支付一元工資,就可以得到若干元的利潤,不管是在農業中挖溝渠,還是在石油業煉油的所得。這是個非常不可能的假說,但卻無法證明這是錯的,因為在資本主義經濟體中,剩餘價值率不是一個可觀察的變數,也不是一個行為的變數。Marx深知這個問題,但急於偽裝這個假說的武斷性,他將價值與剩餘價值具體化,並反覆提及,資本主義體系在全力增加剩餘價值率。這是個體資本主義者做不到,也沒有誘因去做的事。然而,Marx必須假設有一個固定的剩餘價值率,否則他所宣稱的「勞動本身創造剩餘價值」,這個說法會一敗塗地。
至少在西方國家,許多當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,不再相信勞動價值理論,以及剩餘價值勞動理論。儘管如此,身為馬克思主義者,他們繼續相信,資本主義奠基於對勞動的剝削。他們指的剝削,就是工人未擁有自己的生產工具,因此得不到雇用勞動所產生的利潤。他們的說法是,資本主義有個基本的不正義,存在於「工人沒擁有,老闆不工作」這個事實中。我覺得很有意思,去觀察這些自稱「分析派馬克思主義者」能做到什麼程度:放棄各種結果論,讚許資本主義,轉向更多的道德判斷。這些道德判斷的基礎,是資本主義體系內,社會關係的倫理意義。換言之,他們問的是:我們都要工作維生,而少數人可以不做而活,公平嗎?(當然,對此唯一的答案,是非常不公平)。但他們不問:如果沒有不平均且不公平的私人財富分配,資本主義還會創造出前所未有的經濟成長嗎?換句話說,我們可以同意,資本主義並非教化人心的體系,它是粗暴、殘忍、道德淪喪的,但它卻可以產出貨品,而我們要的就是貨品。
2麥卡錫經驗
要不是在1952年遭遇麥卡錫主義(McCarthyism)的幽魂,我懷疑那時我會用這麼多年,來擺脫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力。在冷戰的高峰,美國陷入反共的恐慌中,參議員Joseph McCarthy的聲勢如日中天。從以下的故事可以看出,這是一陣恐慌。1950年我已經從紐約市立大學皇后學院畢業,在哥倫比亞大學唸博士班一年級。當時皇后學院經濟系主任Arthur Gay因車禍喪生,系上找人在學期中接他的課。我曾是他的研究助理,因此被徵詢是否要一試。突然間我發現自己課程滿檔,教授個體經濟學、消費經濟學,以及從沒唸過的行銷學。我還記得每門課第一次上課前,緊張到前一晚真的把內容全部背下來。
正當我的教學開始上手時,由McCarthy主持的「反美國活動委員會」(the Un-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),到紐約調查市立大學系統內的共產主義。他們要求三位知名教授出席,毫無疑問地,是為了問熟悉的問題:「你現在或曾經是共產黨員嗎?」三位教授都援引憲法第一與第五修正案(禁止證人自我入罪),拒絕與委員會合作。儘管三人都是終身職教授,但還是迅速被解職。其中一位是皇后學院的勞動經濟學教授Vera Shlakman。她是我先前的老師,也是當時的同事。「教師工會」(Teacher’s Union),是紐約地區大學教師的左翼職業工會,她左傾也是會長,就我所知,她可能也是對共產主義幻滅的出走者。我上過她的課,知道她小心地保持中立,極力避免灌輸意識形態給學生。幾個學生發動連署陳情書,要求校長讓Shlakman復職。但根據學院章程,請願書至少要有一位院內教師簽署。學生找遍經濟系四十名教授、副教授、助理教授,以及像我這樣的低階助教,沒有人願意簽署陳情書。走投無路之際,他們找上我。出於我對Shlakman教授的尊崇,也因為無法忍受自己的怯懦,我簽了陳情書。二十四小時內,我收到Thatcher院長(奇怪的是,四十年後竟然還記得他的姓名)下的字條,知會我若不立即主動辭職,將會被免職,並列入未來就業的黑名單。
接下來一兩天,我考慮發動大規模抗爭,並發表強力要求個人自由的聲明。這項聲明將傳諸後世,會被美國高中生閱讀、引述。然後,我靜靜地遞出辭呈。
我當時已經走投無路。為了開始寫博士論文,我之前已申請一項獎學金,並仰賴在皇后學院的授課薪水,維持這段期間的生活。在我口袋空空,且因這件事深受打擊之際,突然接獲一通電話,告知我已經得到「社會科學研究會」(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)的獎助金,讓我到國外撰寫博士論文。顯然有人暗中對麥卡錫主義的受害者伸出援手。
我生命中的每個災難,總是以奇妙的方式適時轉化為助力。我很快就了解,生命中最美好的兩年自此展開。我選定「David Ricardo學派在十九世紀經濟觀點的起伏」為題目,最後的豐碩成果,超乎我先前的想像。[1]我也發現,學術研究是自己真正的強項。我在大英博物館附近找個房間,過著中古時代僧侶般的生活,一週七天,每天閱讀、寫作長達十八小時。我將初期的研究成果,寄給博士指導教授,當時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的George Stigler,他辛辣但中肯的評語,正是我所需要的前進動力。兩年後我帶著完成的論文回到紐約,真心歡喜地在電視上,目睹McCarthy參議員最後的傾覆。
1954年夏天,我參加耶魯大學助理教授的面試。日後成為我導師之一的William Fellner是主考委員。我覺得有必要解釋,辭去皇后學院教職的原因。我一直記得Fellner當時打斷我,說:「這是一所私立大學,我們不在意幾年前在公立大學發生的事。」這印證了Milton Friedman的論點:可能的雇主激增後,一個自由的市場,較一個以國家機關為獨買者的社會主義體系,更能確保個人的自由。
今日很難描繪,麥卡錫年代的詭異氛圍。當時在背後捅你一刀的,可能是最好的朋友。人們真的會每天晚上,搜索「床下的共黨份子」。年輕時我曾天真地相信,知識份子會捍衛對抗當權者的想法,但受到麥卡錫經驗的影響,我失去對知識份子與學者的所有尊敬。只要有足夠的壓力,他們會向McCarthy、Hitler(希特勒)、 Stalin、Sadam Hussein,或任何背後有軍警力量的人低頭。
1954年在耶魯執教前,我幾乎已擺脫對共產主義的舊信仰。Kruschev在1956年發表著名的反Stalin演說,我從他親口所說的話,確認自己的新信仰,因而有一種靜靜的滿足感。隨後幾年,我穩定地向右移動,但不像許多前共產主義者,我從未瘋狂地反共產主義。無論是當時,或許直到現在,我依然保持政治上左右擺盪。對私有化、鬆綁、工會立法等政策議題,我相當右派。但對社福支出、失業給付、女性的平權措施、黑人與同志、墮胎權、軟性毒品的合法化等議題,我則是強烈的左派。我向右的旅程,被Reagan與Thatcher阻斷。1980年代居住在英格蘭時,我對政府明目張膽地,用大規模失業來對抗通貨膨脹,愈發感到不齒;也對英國選民十多年來,持續容忍二位數的失業率感到驚訝。Thatcher夫人能用「通膨成本總是大於失業成本」這種說辭,來說服選民、財金記者,甚至許多經濟學家,令我大開眼界。個位數通膨伴隨兩位數的失業率,的確是1980年代的大部分情況,但我相信這是明顯的錯誤。[2]福克蘭戰爭(The Falklands War)已經夠糟了,但她無能力對抗失業問題,或甚至承認這是個問題,讓我面對總體經濟問題時,採取長久以來面對社會問題的左傾立場。正是由於Thatcher夫人,我回到對資本主義有一種近乎穩定的信仰。但這是經過「凱因斯式需求管理」與「準社會主義式福利主義」調和過的資本主義。
3與佛洛伊德的糾纏
深受Marx影響的同時,我也無法拒絕Freud(佛洛伊德)的召喚。1944、1945、1946三年的夏天,我在紐約州北部,幾家以接待猶太客人為主的飯店做服務生。我的客人中,許多是精神科醫師與心理分析師。不久後我就埋首閱讀,Freud及其信徒的作品。佛洛伊德理論解釋所有事物的力量,令我熱血沸騰,這種力量當然也讓我想起Marx的風格。我還清楚記得,目眩神迷於《夢的解析》(Interpretation of Dreams),有感於像夢這般的內在神祕,也可以用理性的方式來解釋。我也折服於Freud的強大文字渲染力,或許人們視他為科學家,但他更是偉大的文學藝術家。佛洛依德主義對我的深層影響,較馬克思主義更長遠。然而漸漸地,這些年來我愈發了解,許多心理分析理論的重要概念,是如何地自我驗證與自我合理化;以及(精神)分析師抗拒以實證測試,來檢視佛洛依德思想的特性。我現在認為,幾乎整個佛洛依德理論,都是胡說八道。再說,作為一種治療技術,心理分析與中國式的洗腦,並無太大差異。但這個觀點的建立,是個緩慢的過程,與我自己的心理分析經驗有關。
W.H. Auden的絕妙好詩〈紀念Sigmund Freud〉,每行都值得引述。Auden的結論是:
如果,他時常錯誤,有時荒謬
對我們而言,他只是個凡人
現在,只是整個意見氣候
在他化身的氣候下,我們過著各自不同的生活
他就像天氣,只可以阻礙或幫助
其實不然,他只能阻礙、也確實在阻礙。
4為什麼要研究經濟思想史?
從小到現在,我一直是個求知若渴的讀者。年輕時用閱讀來逃避,後來養成每天讀一本的習慣。在經濟思想史的領域裡,不斷地閱讀具有比較利益。從這個角度來看,至少對我而言,思想史是一種自我放縱的形式。1954年時,我到耶魯大學任教還不到一年,就被要求接替William Fellner的經濟思想史研究所班,理由很簡單:系上老師只有我躍躍欲試。於是我意識到,二十七歲的我,正在一所頂尖的學府,教一門研究生的思想史必修課。耶魯經濟系那幾年約錄取二、三十位精心挑選的研究生,往後幾年間至少有十二位成為知名的經濟學者。教這門課讓我緊張到過度準備,我在幾年內累積了數千頁筆記,這些筆記後來成為我唯一知名的書《經濟理論的回顧》(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,1962)。
我在這本書的導論指出,思想史學者若非「相對主義者」,就是「絕對主義者」。相對主義者認為,所有過去的學說,大致上忠實反映學說生成的歷史情境。絕對主義者認為,思想的變遷是這門學問內部邏輯發展的成果;以日後的眼光來看,早先的思想幾乎都是錯的。我宣稱自己是個抬頭挺胸的絕對主義者,並在書中消遣相對主義者。然而,這已不是我現在的觀點,原因是這些年來,強勢的「輝格歷史詮釋」(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),已經搶盡風頭。近年來我目睹許多論述者,嘗試以現代的外衣包裝(特別是某種數學模型),來重現過去的偉大思想。我於是理解到,過度的絕對主義邏輯,將會抽去思想史的根本。絕對主義完全不懂得珍視過去,而且不合理地要求,歷代的思想家必須活在今天,並以我們的方式思考。這種做法會摧毀對歷史的認知。
我年輕時期的絕對主義,是三股力量作用的結果。第一,1950年代末期與1960年代初期,經濟學這個領域的信心達到頂峰。我們「當時」知道:就理論而言,一般均衡理論的簡潔已經達到極致;投入產出分析與線性規劃,很快就會讓一般均衡理論不只簡潔,並具有可操作性;「新古典綜合」已經成功地將凱恩斯總體經濟學,加進華爾拉斯派的個體經濟學。簡言之,真正的經濟學是個教會,所有的真理隨時會展現在我們面前。就經濟思想史而言,如果有人要採取絕對主義的觀點,1960年正是絕佳的行動時間點。第二,我深受Schumpeter的《經濟分析史》(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,1954)影響。Schumpeter當然是個奇特的絕對主義者,然而他也是個執著的絕對主義者。我之所以強調Schumpeter,是受到博士論文指導教授George Stigler的作品與人格影響。[3]當時Stigler打擊學生的惡名在外,但我們的關係始終良好。我喜歡強勢自信的人。當他說你寫的東西是胡扯,提出許多尖銳的批評,來支持他的判斷,讓你不得不感激,他竟然紆尊降貴地批評你。他也是我認識的人當中,極少數真正有趣的人。他的幽默感戲謔甚至惡毒,但我喜歡。我發現自己在模仿他的授課風格,當然還有他的寫作風格,但是我總寫不出像他那般犀利的註腳。
往後每當我遇到他,立刻變成屈膝的年輕研究生。其實我有點怕他,特別是我們的政治觀點相差十萬八千里,有好幾次我還不經意地,表達讓他深惡痛絕的意見。他最令我感動的回憶,是1960年在芝加哥時,把我介紹給他在1930年代的指導教授Frank Knight。我看他跟Knight講話時的恭謹,與我面對他時的態度若出一轍。我忽然了解,就像我無法把Stigler當成平輩一樣,Stigler也無法與Knight平起平坐。這種師生之間「知識明燈」的傳遞不息,有極其動人之處。
先不論絕對主義有什麼知性上的長處,除了Schumpeter與Stigler,我在耶魯的學生,也是將我推向絕對主義的動力。經濟思想史在1950年代,是研究所的必修課,這些典型的美國研究生,只想學現代經濟學的工具與技法,完全不在乎經濟史和思想史這類學術性的科目。我從一開始就知道,要說服這些熱血青年接受思想史,就必須讓他們感受到,在某種程度上思想史與他們相關。所以我教這門課時,不僅強調純粹分析的概念一脈相承,不斷強調過去思想的現代性,同時也坦承過去的思想有時缺乏現代性。
我非常用力鼓吹,經濟學史是追求知識的合理學科,但這項努力也消磨了我對經濟學史的興趣。1962年我離開美國之前,我已大致決定轉攻應用經濟學。但在離開思想史十年後,我在1970年代重新擁抱這個最初也是最後的戀人。總而言之,我發現思想史在知性上所帶來的滿足感無可匹敵。我一直不能明白,如果我不知道某個思想的來龍去脈,我怎麼可能真正了解這個思想?我開始學微積分時,就必須探究牛頓是怎麼發明它的?Leibniz是如何獨立發明它的?雙方如何論辯正確的微積分符號,以及導數這個概念的意涵究竟為何?儘管一再努力,我一直無法真正了解,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,原因是十九世紀末的物理學對我太難,因此我無法像理解Leibniz一樣地了解愛因斯坦。經濟學和其他學科的偉大理論一樣,套用經濟史最近流行的術語來說,都是路徑依賴(path-dependent)的。也就是說,要解釋為什麼會產生這些偉大的思想,就必須先理解過去的文獻,如何導出新的理論發展。如果當初的思想主體不同,就會發展出不同的理論。換句話說,沒有經濟思想史,新的經濟理論怎麼可能從天而降。除非你願意無條件地接受新經濟理論,否則你一旦想評斷它,就必須問它是從哪來的,而這個問題只有思想史才能回答。
我很了解,在經濟學家論資排輩的行列中,思想史學者為何寥若晨星。但這確實意謂,對大多數經濟學家而言,這是幾乎非知識性的學科。許多經濟學家面對思想時,簡直不知人文為何物,就像山頂洞人聽貝多芬四重奏曲時,還問為什麼這四個演奏者,似乎無法齊一拉弓。
5教育經濟學
1962年我拿到研究獎學金,從美國到巴黎一年,繼續十九世紀的棉業研究。那年年底是耶魯升等的年限。在美國的大學擔任助理教授六年後,學校必須擢升你為終身職副教授,或是請你離開。耶魯不讓我升等的原因,是他們不需要專攻經濟思想史的資深教授,我覺得有必要另尋出路。現在想到回美國這件事,就讓我感到灰心。我了解到,即使在美國生活二十年,我始終認為自己是歐洲人。對我來說,美國人太粗線條、太市儈。面對那些粗鄙的美國人,我還存有些許身為文化歐洲人的優越感。如John Stuart Mill所言,在美國「男人全心搶錢,女人全心餵飽男人。」;或者如Oscar Wilde所描述,美國「這個國家,從野蠻直接跳到墮落,缺少中間的文明階段。」我決定搬回英國,那個我在二次大戰期間渡過男孩歲月,與之後寫博士論文的地方。
我開始申請幾個英國大學的教職,但1962年的學術就業市場沒什麼擴張。我很快就了解,可能過了一年都找不到工作。我幸運地碰到倫敦大學教育學院(University of Lond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)院長Lionel Elvin,他告訴我教育經濟學在英國是個新領域,他們有個員額一直找不到合適的人。我從沒聽過「教育經濟學」,決定先做些功課。我沒花太多時間,因為在1962年時,這個領域的研究極有限。我勇敢地寫信給Lionel Elvin,坦承是教育經濟學的新手,但想知道教育學院,能否以一或兩年為期約聘我。院方同意,且出乎雙方的意料,這兩年結果變成23年!我提這些事,只是要強調意外在人生扮演的角色。我讀過幾十種複雜的理由,來解釋人們如何選擇工作或婚姻。經過仔細的研究,我發現經常是純粹的機緣成為化學家或律師,或選擇另一個她或他成為伴侶。
倫敦大學教育學院,是學士後教師進修學院,學生大都是想要升級的老師,我的授課時數不多。教育學院經濟系只有兩三個成員,我的行政工作負擔也輕,首度可以全心投入寫作與研究。雖然沒有經濟學家可以對話,但倫敦政經學院(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,LSE)就在同一條街上,因此也不以為苦。不久後我就到倫敦政經學院兼課,我的時間就平分在兩個學院。
對我來說,教育的世界是個全新的範疇,比經濟學的世界更軟性。極少教育學者重視,以實證結果來支持自己的主張,有許多論證淪為價值判斷的衝突。面對教育學者對經濟學家的切齒敵意,我一開始沒有作好準備。在他們眼中,從好的方面來看,經濟學家是成本的撙節者,從壞的方面來看是法西斯人渣。見風轉舵的情況,在教育學界甚至比經濟學界更嚴重。儘管在政治的光譜上,教育學的重心位置,遠較經濟學偏左,但當教育學者向右靠時,他們讓Milton Friedman看起來像是左翼怪咖。
不久後,我就開始強力鼓吹人力資本理論(human capital theory)。我也是對英國的教育投資,進行報酬率計算的第一人。大約在1965-75年間,我為人力資本論陣營廣招信徒並全心投入,至少在文章發表的數量上打敗對手。然而就像先前的佛洛依德主義與馬克思主義,人力資本論的神話也宣告幻滅。1976年我發表一長篇檢討報告,其標題「人力資本理論︰不堪回首的記錄」,即可說明一切。這篇文章指出,人力資本理論沒有錯,但立論薄弱且未見成果,無法呼應這個理論早期提出的承諾。也無法與主要的競爭對手(篩選假設理論、文憑主義、文憑熱,隨你怎麼稱它)匹敵。最後我認為,人力資本論大幅誇大認知知識,在教育的經濟價值中,所扮演的角色。教育心理學者說,正規教育能賦予「情緒行為特徵」。也就是說,學校在形塑學生價值與態度過程中的影響,可以解釋現代化的過程中,教育的經濟、甚至社會、政治角色。雇主看重教育的部份,不是在受過教育的職工知道什麼,而是他們如何表現。這個領悟,深遠地影響了職業訓練的議題與教育計畫的面向、甚至教育資金的問題。我的「不完全契約」概念,需要監督「人類努力」(human effort),以及職工雇用與晉升所涉及的篩選、傳遞問題。最後,我將這個概念,與我對教育的經濟價值的新觀念相結合。但是在1970年代末期前,我發現自己在不同場合一再重複這些訊息,無論是對教育社群,或經濟學家處理教育議題的方式,皆未產生絲毫影響。結果是我對這整個議題失去興趣。
的確,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,我都覺得教育比起絕大多數的議題,更容易淪為一種似曾相似、沒完沒了的連環歹戲。其中的每個問題與論點,每隔十或二十年,恆常以相似的形式重複出現。這種現象的例子不勝枚舉,我只提一個。1960年末期,我開始倡議高等教育的學生貸款。這種學生貸款的財源,最好來自畢業生就業生涯中,所課徵的畢業稅。儘管在那之前,高等教育的學生貸款在美國已經是老套,但在英國一直到1980年代,這還是個聳人聽聞且極端不受歡迎的想法。我曾經非常接近英國教育的權力中心,首先是1970年代初期的工黨政府,接著是1980年代初期的保守黨政府,但是從未成功地讓有能力執行的人接受這個想法。1982年左右我憎惡地放棄它,但其他英國經濟學家立即接棒,更有力地鼓吹它,到最後還是無力回天。Thatcher夫人的保守黨政府,1988年終於通過一項陽春型的學生貸款計畫,讓學生在十五年內清償個人債務。當時對這個議題二十年來的相關論述完全沒提到,英國經濟學界毫無批判地接受這個提案。直到今日政治人物還普遍認為,高等教育的財務並非經濟學家的強項。
在教育學院任教這些年,我花了許多休假時間,在亞洲與非洲擔任聯合國各種組織的教育顧問。這些組織包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、聯合國亞洲暨遠東經濟委員會、國際勞工組織、世界銀行。我參與經濟代表團,前往赤道非洲、南亞、東南亞等地區的六個低度開發國家。我在印度待六個月,寫一本關於畢業生失業的書,在泰國與印度為福特基金會工作一年。對發展經濟學,以及提供第三世界國家經濟諮詢,起初我學到很多東西。然而學習的報酬遞減效應很快就出現,而且發現我一直在重複,幾乎每件在前個國家工作時所說的話。我開始時滿腔熱血,亟欲拯救第三世界的塗炭生靈。但隨著時間的消逝,我愈發同意Peter Bauer的看法,那就是對第三世界的援助,害之甚於愛之。聯合國的援助使團也好,建議第三世界國家,哪些經濟政策要做或不做的諮詢也罷,這一切都不過是一齣超級大戲。這些相關國家,只想得到援助或世界銀行的貸款,但到手前要先證明,他們已經盡力尋求諮詢。除了石油鑽探或水利工程等技術領域,這些國家不花錢向國際顧問業購買諮詢服務。他們找聯合國組織,爭取像我這樣的特約顧問提供服務。我很快就識破他們陽奉陰違的兩面手法,但至少還做了一陣子正事,直到他們高唱的歌曲變調。
我越來越不相信,那些我必須共事的第三世界部長與政客。他們利用我這樣的經濟學家,去得到想要的援助,同時中飽金援的餘款。在每個曾工作的國家,目睹這些貪污與政治假面,終於讓我反對發展諮詢顧問這件事。要脫身容易,只要說些第三世界政府不想聽的話,而且說得夠勤快,就保證不被續聘。
我念玆在玆的事很簡單:堅決反對高等教育,強烈支持小學教育。我認為這些國家,特別是其中的非洲國家,在免費的高等教育上離譜地透支經費。當然,這些政府的當紅官員,之前都曾因此而受益。同樣離譜的是,這些國家的偏遠小學經費不足。另一件令我在意的事,是中學階段正規職業教育的浪費,更不要提小中學課程標準的職業化。如果認為學生的知識,造成教育的花費如此昂貴,那真是長久以來的謬誤。以上兩個錯誤政策的成因,是一種稱為「人力需求法」的教育規畫技術。人力需求法是把投入產出分析,不適切地用來媒合受教育職工,以及個別產業的工作職位。我用了十多年的時間,攻擊人力需求法教育規劃,最後還是未竟全功,至少在第三世界是如此。人力需求法完全針對物質量(physical quantity),完全不談價格(有人名之為無價經濟)。這個方法淺顯易懂,在政治上無可阻擋,因此直到今天,還是第三世界教育訓練計畫的主要工具。
擔任第三世界顧問這些年,領受到一個重要教訓。那就是社會主義的目標,與發展現代化的目標結合時,所產生的嚴重歧異。我曾效力過的每個政府,對社會主義都懷抱某種程度的使命感,但也想要進行現代化,與仿效美、日、英等國家。這些國家侈言「在地創業家精神」之必要,但卻壓制每個賺錢的人,特別是出售黑心貨品給在「非正式部門」的一般人民。簡言之,他們從未能接受「徹底個人主義」,以及快速經濟成長所帶來的不平等,但也無法放棄成長與發展的目標。他們完全搞不清楚「國富的肇因」,不管這些「肇因」為何,絕對不是立即杜絕「非勞動所得」,也不是所得非配的完全均等。
令人啼笑皆非的是,在1970年代時,幾乎每份我幫忙撰寫的經濟使團報告,都是由獨裁者統治的國家委託。這些獨裁者在報告剛發表,或不久之後就被推翻,列舉如下:1964、1976年,聯合國教科文組織「世界實驗讀寫能力計畫代表團」,赴巴勒維國王轄下的伊朗;1972年國際勞工組織「世界就業計畫代表團」,赴Haile Selassie轄下的衣索比亞;1973年國際勞工組織「世界就業計畫全面代表團」,赴馬可仕總統轄下的菲律賓;1975年國際勞工組織「世界就業計畫全面代表團」,赴El Nimeiry總統轄下的蘇丹;1976年國際勞工組織「世界就業計畫代表團」,赴Moshoeshoe國王轄下的賴索托;1981年聯合國開發計畫署代表團,赴Wanghuk國王轄下的不丹;1983年聯合國開發計畫署代表團,赴蘇丹Bolkiah轄下的汶萊;1983年世界銀行代表團,赴鄧小平轄下的中國。寫作本文同時,除了不丹、汶萊、中國,其他國家的領導人皆已換人。當年寫報告的對象,常常被現在掌權的人視為仇寇。經濟學家對外國政府的經濟政策具有影響力,這個觀念已經不再成立。
6經濟學方法論
隨著1970年代的展開,我逐漸轉向經濟哲學方法論,這也成為我長期的研究興趣。其實這是我一直不自知的興趣,始於我年少時對馬克思主義的著迷,更確切地說,始於我對馬克思主義的幻滅。皇后學院大四那年,我修一門Donald Davidson的社會科學哲學討論課(我後來才知道,Donald Davidson是個望重士林的科學哲學家)。Davidson知道班上有幾個青年馬克思主義者(別忘了當時是1949年),他處理馬克思主義的方式就是溫和地戲謔它。當我使出Hegel辯證三法則(量變到質變、對立的統一、否定的否定),作為打開所有門的萬能鑰匙,他提出更好的Herbert Spencer的演化「法則」︰演化是由一個相對地模糊、不連貫的同質性狀態,改變成為一個相對清晰、連貫的異質狀態。Davidson說:「這乾淨俐落地幾乎解釋了每件事。」我驚訝地明瞭到,這跟辯證法則一樣地真實:它們解釋了每一件事,那就等於什麼都沒解釋。
Davidson要我們讀Carl Hempel的論文〈歷史中一般法則的功能〉(“The function of general laws in history,Journal of Philosophy,1942,39(2):35-48)。Hempel指出,要合理解釋歷史現象(例如法國大革命),必然要援引某種普遍的實證假說,且該歷史現象被認為是這個假說的特定例子。若無法做到,那就只是偽說明(pseudo-explanation)。後來這被稱為「科學說明的涵蓋模型」(the covering-law model):解釋一件事,就是將它「涵蓋」在某種普遍法則之下。四十多年後,我還記得這篇論文如雷轟頂。包括此文在內的十幾篇文章,對我的思想有長遠影響。我忽然了解,多年來我一直用這種偽說明,而不了解它們站不住腳,因為它們涉及我或其他人,都一無所知的那種涵蓋法則。一個革命性的涵蓋法則?是的,我們都讀過Crane Brinton的《革命的解析》(Anatomy of Revolution,1938),這本書以三個革命為樣本,歸納出革命的通性。但這些通性幾乎不等同普遍法則,或甚至普遍可應用的特性。簡言之,除了以隨機的方式,沒有人真正解釋過法國大革命或俄國革命。
我寫博士論文之前沒讀過Popper,但已經多少吸收過他的否證主義(falsificationism)。這個概念有些來自Milton Friedman的經典論文〈實證經濟學方法論〉(“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”, 1953)。雖然這篇文章沒提到Popper,卻是一種粗糙、迷你版的Popper主義。這個概念也有些來自Stigler論經濟思想史的文章。1954年我在耶魯任教後,很快就與Tjalling Koopmans交好,一方面因為他是業餘作曲家,我也開始拉大提琴,我們可以談音樂;另一方面因為我們都來自荷蘭,喜歡一起講荷語,但我們對經濟學的興趣完全不同。他開始寫《三論經濟科學的狀態》(Three Essays on the State of Economic Science,1957)的第二論時,內容全都是關於方法論。我們談到Friedman的論文,我第一次完全被預測主義說服。預測主義指的是,理論的有效性,必須以它的預測正確性來評斷。1956年我發表第一篇專業論文〈李嘉圖經濟學的實證內容〉(“The empirical content of Ricardian economics”),內容充滿預測主義,然而我還是沒唸過Popper。我能恍如昨日般,記得最後決定唸Popper的那一刻。
1962年住在巴黎時,一個週五下午我逛進書店,看到Karl Popper的《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》(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,1945)。眾所周知,這本書是研究Plato、Hegel、Marx這三位開放社會的大敵。我回家吃過晚飯馬上開始看,整個晚上加上週六整天都看,滿心不願意地睡著,週日把它看完。我敢說在那之前,或之後直到現在,沒有一本書讓我更熱血。[4]讀它就像是暢飲一瓶香檳。這本書右打Plato和Hegel(我一直將兩人視為右派怪物),左批Marx犯下「啟示錄型的謬誤」(預測在未知的將來某一天,世界末日將到來的遊戲)。它也提供科學哲學、否證主義以及反對政治革命的有力論述。反政治革命的原因是,整體來說,我們缺乏改變社會的知識,但我們可以也應該,以漸進的方式來改革社會。
於是我坐下來,閱讀Popper寫的所有東西。我成為徹底的Popper主義者,雖然我現在覺得Popper有下列誇大之處:(1)沒有歸納法這回事;(2)檢證法(verification)與否證法(falsification)之間,有根本的不對稱性;(3)方法論是規範性的,且與科學史無涉。直到今天,我還是個不再生(unregenerative)的Popper主義者。我在Popper身上學到,怎麼用清晰素樸的正統英式英文,來論述複雜的議題,也發現自己幾乎是逐字模仿他的風格。[5]1952年去倫敦寫博士論文時,我興奮地得知Popper在倫敦政經學院,每週一次開科學史的討論課。我獲准列席旁聽,但很快就了解Popper是個舊派普魯士風格的老師。他在著作中苦口婆心反對傲慢的偏執,然而他自己就是活生生的反證。倫敦政經學院流傳著一則笑話,顯然是Popper學生想出來的。那就是Popper應該將他的書定名為《一個開放社會的敵人的開放社會》(The Open Society by One of Its Enemies),較好的書名是《一個封閉心靈的開放社會》(The Open Society by a Closed Mind)。唉!最偉大的作曲家Beethoven,是個糟糕的人,Wagner、Goethe、Tolstoy亦然,我自己也好不到哪裡。
7經濟學之前是哲學
我從不後悔年輕時立志成為經濟學家,但有些時候我但願當年唸的是哲學。我可以說是始於哲學,也似乎是終於哲學。我的開端並非一般性的哲學,而是一種特定的哲學:神學。「神是否存在」是我第一個問與答的哲學問題,至今我仍感到興趣。我被養育為正統猶太人,十二歲前信泛神論,十五歲前信不可知論,十七歲前信激進無神論,自此未曾片刻動搖。的確,年紀愈長,我的無神論似乎愈激進。現在當我舌戰超級信徒(不得不說,我愛、超愛這麼做)時,要同時維持有禮合宜的談吐,簡直是對我容忍力的一大考驗。
這一切的開始是我十二歲那年,叔叔給我一本《聖經》,我沒留意裡面有新約與舊約。我是個停不下來的讀者,一書在手就全心投入。我從來不知道新約的存在,很自然地就讀起來。我立刻被耶穌的故事深深吸引,再輔以閱讀Ernest Renan的《耶穌的一生》(一本十九世紀美化的耶穌傳記,將他描繪為人性化的遠古先知)。我認為這個說法必定為真,但親戚都告訴我這個說法是假。我與他們爭辯,然後被送到拉比(猶太教經師)處接受矯正。他很快地說服我,指出耶穌不可能是神的兒子,因為創造宇宙的至高智能,既不能有子嗣也不能是彌賽亞,原因是當彌賽亞降世時,羔羊將與獅子並臥,放下刀劍,民族間不再兵戎相見。刀劍放下了嗎?民族間的戰爭停止了嗎?於是我發現,那是個具有徹底說服力的論證。
也許在福音故事裡,記載的耶穌美麗故事是假,但是佛陀的故事呢?佛陀是耶穌之後的下一個閱讀,我覺得兩個故事同等美麗。然而親戚友人再一次告訴我,佛陀的故事不可能為真。所有這些美麗的故事,包括舊約中摩西、約瑟、大衛的故事、新約中耶穌的故事、以及大乘佛教經典中的佛陀,我想必然都是真,因為它們這麼優美。然而同樣地也必然為假,因為它們彼此的矛盾。我茅塞頓開,不再相信任何權威性的宗教,而成為Spinoza式的泛神論者(我當然從未聽過Spinoza)。1940年德國入侵後,我們倉皇離開荷蘭,父母把哥哥跟我送到英國寄宿學校。校長是個基督教科學會信徒,試圖要我改信基督教科學會,這件事讓我接觸權威式異議教派。往後幾年,我是大人眼裡經常性的小搗蛋鬼,因為我從不停止問他們宗教信仰的問題。我發問的目的不在學習,而在說服他們放棄,證明神存在的設計論證(argument of design)、第一因(first cause)論證、或終極目的論證等謬誤。至於耶穌的歷史性,我有很多聰明的理由,來說明耶穌存在的可信度,比不上亞瑟王或羅賓漢的可信度。我必須說,這是我永遠無法真正學會克服的弱點。直到今天,我忍不住要跟基本教義派份子辯論,無論其背景是基督教、猶太教、伊斯蘭教、或印度教,儘管我知道這是無望的白費力氣。我是個地獄的(infernal)樂觀主義者,總是相信理性的論證最終會勝出。
我喜歡把自己描述為一個宗教的人,意思是說,我每天都在思索以下的大哉問:宇宙間有秩序嗎?這個秩序意義何在?我們活在世上是為了一個目的嗎?這些都是好問題,但是由神或教會來回答,對這些問題的深度而言是一種污蔑。我十幾歲時熱切擁抱馬克思主義,其中一個原因是他的無神論正是我所要的。我閱讀Popper,想要親近Popper作品的原因,並非Popper主義等同無神論,而是Popper的謬誤法完全適合無神論。請讓我看看有哪些事件,可以推論神不存在?沒有,當然,神的存在是信仰的問題。我們相不相信神的存在並不重要。不會造成區別的區別,是無意義的區別(A difference that makes no difference is no difference)!故此理得證。
8從Popper到Lakatos
1960年代後期,當我固定在倫敦政經學院授課時,認識了Imre Lakatos。他繼Popper之後,在倫敦政經學院擔任邏輯與科學哲學教授。在這短短幾年間,我很喜歡他(他1974年去世)。1968年的學潮期間,他成為無懼卻具同情心的批判者,毫不憐憫地取笑學生的激進虛矯行徑。他有資格這麼做,因為在1956年逃往西方世界之前,他曾經因「右派偏離份子」的罪名,在匈牙利監獄服刑數年。他有極佳的幽默感,[6]我們一見如故十分投緣。Lakatos不懂經濟學,但他的博士生Spiro Latsis給他靈感,想把他的方法論見解應用到經濟學領域。Latsis的確是首位將Lakatos思想應用在經濟學的人。1974年 Lakatos在希臘辦一場學術會議,讓物理學者、經濟學者、科學哲學學者,發展一些「科學研究方法論計畫」的個案研究。他在會議召開前一個月猝逝,Latsis如期舉辦這次會議來紀念Lakatos。對我和其他許多人來說,這次會議是一生難得的際會。經濟學領域有Lionel Robbins、John Hicks、Terence Huchinson、Herbert Simon與Alex Leijonhfvud等大家。哲學領域有Carl Hempel、Adolf Grunbaum、與Paul Feyerabend等碩儒。充滿知性的火花。會議召開的地點,是希臘境內美麗的Nafplion。Spiro Latsis的父親John Latsis,豪邁地提供金援,讓我們見識一種心嚮往之的風格。
Popper與Lakatos兩人之間關係的爭議,自1974年起延燒至今。在我眼中,Lakatos是80%的Popper,加上20%的Kuhn。Lakatos強調不同的東西,但傳達的方法論本質上與Popper相同。1989年Neil de Marchi和我在Capri籌辦第二次Nafplion會議,與會的眾多經濟學者,對Lakatos與Popper思想的敵意讓我深深訝異。大部分的敵意,是針對Lakatos堅持,說對科學研究的最終評判,應該以能否創造出嶄新的預測為指標。這個標準終究難以被與會者所接受,他們了解這個指標會讓今日通行的新古典經濟學,幾乎全部都會被質疑。
逐漸地,經濟學自1950年代以來,近年來更是以加快的速度,變得愈來愈數學形式化。也就是說,幾乎都只關切分析的精準,而不惜犧牲政策的相關性。經濟學所展現的,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社會數學,而非實證的社會科學。經濟學家有時被指控為物理羨妒症(physics-envy),但這是完全誤導性的指控。任何了解當代物理的人都會證實,物理學重視實驗證據,力求理論與實驗證據一致,不太重視嚴謹的定理與分析的引理(lemmas)。經濟學家的真正問題,是數學羨妒症(mathematics-envy)。一般均衡理論是經濟理論中最尊貴的類型,只有這個領域的頂尖專家在運用。這個理論完全不具實證內容。證明多重市場與一般均衡的存在、獨特性、以及局部的穩定性,能幫助我們對經濟體增進多少了解?完全沒有。沒有物理學家會認為,一般均衡理論提出有趣的問題,但數學家當然會發現這是一展身手的機會。一些當代的一般均衡理論學者,甚至將之合理化,說它實現了Adam Smith的古老承諾,證明「看不見的手」有調和私人與社會利益的傾向。這種說法不僅歪曲知識史,也完全誤解競爭作為社會過程的重要性。這個社會過程發生在現在,在一個以私人企業為基礎的經濟體系,這個社會過程也確保科技動能和成本極小化。Walras式的一般均衡理論,或是最終狀態(end-state)理論,與上述的說法根本不相干。
浸淫在經濟學領域45年後,最令我驚訝的是,儘管一般均衡理論未能實現其目標,且持續將科技進步剔除在經濟研究的題目之外,它依然享有高度評價。近年來,經濟史學者終於開始打開科技變遷的黑盒子,但經濟理論學者持續研究經濟成長,彷彿經濟成長全都是資本與勞動力增加的結果,而且僅是生產要素的量化增量(quantitative increments)。從一位二十世紀經濟學的中心人物身上,可以充分看到這種過分強調Walras式一般均衡理論,而輕忽科技進步的典型。這個人物就是Joseph Schumpeter。奇怪的是,Schumpeter一方面非常推崇Walras式的理論,將它視為經濟學術成就的巔峰。另一方面,Schumpeter對經濟學的原創性貢獻,幾乎未受到Walras式理論的啟發。的確,講實在的,Schumpeter與Walras的貢獻是相互衝突的。當我比較年輕時,對Schumpeter的創業家精神理論,與對創新學說的處理,並未給予太高評價。但從那時起,Schumpeter在28歲寫的《經濟發展理論》(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, 1911),就被我視為二十世紀經濟學的巨著之一,足可與Fisher的《利率論》(Theory of Interest)、Keynes的《一般理論》(General Theory)並駕齊驅。Schumpeter有兩項天才的洞見:(1)過程創新只是創新的一個類型,在經濟成長的重要性,可能還遠不及產品創新或組織創新。[7](2)他認識到銀行信用,在企業家精神的推展中,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;對由機器驅動的工廠生產來說,銀行信用不只是財務的附屬品。誠然,Schumpeter頌揚企業家精神,幾乎將它簡化為傑出個人的英雄主義,但是無論如何,談論資本主義下的經濟進展, Schumpeter比Marx以降的任何經濟學家都更有貢獻(就過去一百年的經濟理論化,這是多麼悲哀的評論!)。Parato最適、完全競爭、靜態效率等等,是受到一般均衡的啟發,也是備受讚譽的福利經濟學第一與第二基礎定理。Schumpeter卻認為這些都不具實際的重要性,因為我們是藉由可行的競爭標準、動態效率、科技動能等,來評估市場的結構:那就是Adam Smith所說,競爭的「看不見的手」的意思,而非消費的邊際替代率,等於生產的邊際轉化率。
令人憂心的是,後現代結構在方法論的概念上,成為一組受歡迎的描述性規範。這證明當代經濟學,充斥著無結果的數學形式主義(sterile formalism)。Donald McColskey已經告訴我們,經濟學只是強辯硬拗,和文學批評或美學沒什麼不同。經濟學認為,某些「深描」(thick)的方法論規則(輕聲說話、傾聽對手、提出論證),還可以接受;但是Popper與Lakatos的「淺繪」(thin)方法論,就被判定為不合理。McColskey或他的追隨者從未覺得,這是個破綻百出的見解。
我並未把Popper與Lakatos,尊為作品不能被質疑的大師。我確信他們的有效貢獻,核心是以下的概念:經濟學必須處理現實世界的問題,而達到這個目標的最好方法,就是推出具有「實證上可以被推翻的理論」。那並不表示,達不到上述要求的分析概念,就必須立即被丟棄。我們必須努力創造可以被否定的預測,同時不能滿足於未經實證質疑的經濟理論。科技的解謎,若只是一種為解謎而解謎的遊戲,就不能像現在這樣,成為學生的模範。
在我的專業經濟學家生涯中,我一直欽羨Milton Friedman做學問的風格,卻不齒於他的政治觀點;我欽羨Paul Samuelson的政治觀點,但不欣賞他的經濟分析手法。我似乎註定永遠要陷於兩難之間。
[1]我的博士論文Ricardian Economics 出版時(1953),我認為David Ricardo是嚴謹的理論家、令人景仰的人物,還以David為我的大兒子取名。這些年來我開始發現,Ricardo有「可伸縮」(telescopic)的傾向:將長期縮為短期,之間沒有轉換期。這是正統經濟學的持續之惡。
[2]在哥倫比亞大學唸研究所時,我開始對通貨膨脹經濟學感興趣。當時的老師Arthur Burns教總體經濟學,對Keynes的理論多所質疑。Burns是我博士論文口試的四位委員之一(其他三位是Abram Bergson、John Maurice Clark與Karl Polanyi)。Burns問我通膨問題何在?這是個奇怪的問題,因為當時美國的通貨膨脹率1%。無論我給任何答案(對債主不公平、對薪資員工與年金領取人造成問題、一種儲蓄稅等等),他就以一個反證來駁斥。不到十分鐘,他讓我不知所云,覺得自己像是個兩呎侏儒。意識到必定過不了這部份的口試,我的心涼了半截。最後我被告知通過整體口試,我因通膨問題的差勁表現向他致歉。他親切地拍拍我肩膀,說:「沒關係,年輕人,比你強的人都栽在這個問題上。」我衝回家,狂讀通膨問題,矢言永不再敗在這個問題上。
[3]我在哥大所有的老師,包括James Angell、Arthur Burns、William Vickrey、John Maurice Clark、Abram Bergson、Ragnar Nurkse與Karl Polanyi,其中我只清楚記得Karl Polanyi。因為他介紹一般經濟理論,要我唸從未聽過的書(例如Malinowski的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),並教我如何輕而易舉地杜撰歷史「法則」。Polanyi注重「互惠」與「再分配」,他以這兩個術語,描述歷史上所有市場經濟之前的經濟體系。我不相信The Great Transformation(1944)的中心論點,但它是氣味相投的「中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」,且非常引人入勝。
[4] 「最喜歡的書」。這是我喜歡玩的維多利亞室內遊戲:(1)最喜歡的小說:Homer的Odyssey。(2)最喜歡的詩:Stephen Spender的 ‘I Think Continually of Those Who Were Truly Great’。(3)最喜歡的戲劇:Arnold Strindberg的The Father。(4)最喜歡的軍事史:William Prescott的The Conquest of Mexico。(5)最喜歡的思想史:Arthur Koestler的The Sleepwalkers。(6)最喜歡的哲學作品:Alfred Ayer的Language, Truth and Logic。(7)最喜歡的人類學研究:先前提過的Malinowsky。(8)最喜歡的政治研究︰ Popper 的Open Society;等等、等等;這是無止盡的遊戲,困難之處在於你不能選第二名。
[5]更令人尷尬的文字風格啟發者是Joan Robinson。第一次讀她的經濟學著作是在學生時代,多年後我還是深受吸引。我讀過她寫的每個字,她的語言(充滿素樸口語的文字代數),吸引我的程度,跟她政治觀點倒我胃口的程度一樣。我們碰面時,她總是對我極不客氣(在1960年代「劍橋的資本理論爭議」後,她即視我為敵),但我不在意。在經濟學這個由男性主導的專業,要當個聰明的女性已經夠難了;要在劍橋經濟系這種同質氣氛中當個聰明的女性,鐵定令人抓狂。
[6]我最喜歡的Lakatos故事,帶有精采猶太笑話的強烈色彩。Lakatos說他成長在一個匈牙利小村莊。七歲時帶第一張成績單回家時,所有的科目都得到A,唯有體育是C。他媽媽狠狠揍他一頓以示懲罰。隔年的成績單,包括體育在內,通通得A(故事講到這裡,已經夠好笑了,因為他體型瘦小,根本不可能在運動上有傑出表現)。母親總是告訴他,希望有一天他可以成為劍橋大學教授(不知為何,她將劍橋視為學術成就的巔峰)。1956年Lakatos從匈牙利逃到英格蘭,獲得獎學金赴劍橋攻讀數學史。他完成博士學位(論文以Proofs and Refutations為書名出版),並獲聘為臨時講師。他將寫信告知住在匈牙利的母親,她回信說:「好,但他們為什麼不讓你當教授?」
[7]我了解產品創新的重要性,是基於個人因素。1930年代我父親在荷蘭做雨衣,材料本來都是人造橡膠。1932年,一個瑞典人發明了府綢(poplin)雨衣,徹底改變了這門生意。隔年是荷蘭經濟大蕭條的谷底,父親發現手上有好幾千件賣不出去的橡膠雨衣,瀕臨破產。雨衣產業的人都認為風潮不會長久,但父親是個悲觀主義者,他相信橡膠雨衣的需求不復存在。於是將所有存貨,賤價賣給阿姆斯特丹最大的服飾店C&A。C&A對父親的大膽印象深刻,表示若他有能力學會生產府綢雨衣,願意下訂單。父親前往瑞典,挖角一個裁縫師和剪裁師,完成那筆訂單。接下來,訂單一筆接一筆。1935年之前,他已經成為荷蘭的雨衣大王、白手起家的百萬富豪。他的好運並不長久,1940年代德國人入侵荷蘭,我們失去一切。這個發跡致富的故事開始時,我六歲;故事結束,十二歲。簡言之,我有充分的理由,相信新產品的影響力。